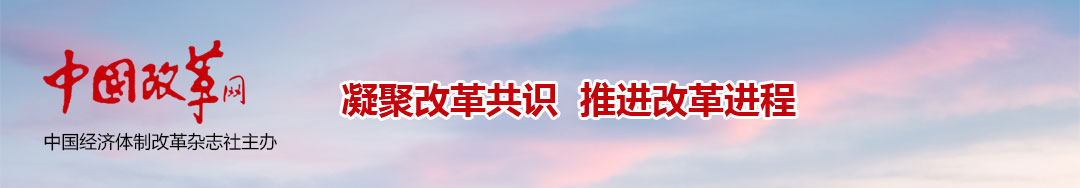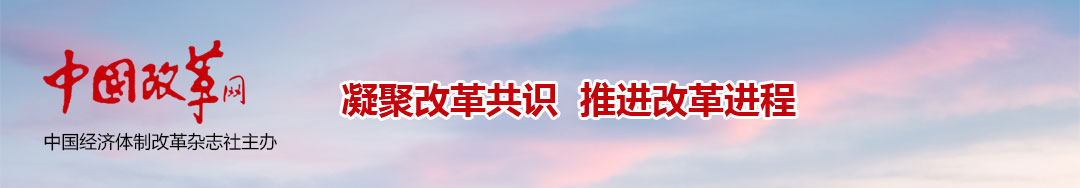國家與社會協(xié)同治理的實質(zhì)��,就是政府與公民對社會政治事務(wù)的合作管理����,簡單地說����,就是官民共治��。這些年來���,包括政治學(xué)界在內(nèi)的中國知識界越來越重視并倡導(dǎo)國家與社會的協(xié)同治理或官民共治����。這決不是知識分子的標新立異��,也不是他們不懂中國國情����,更不是敵對勢力“西化”“分化”的結(jié)果���,不是西方的“陷阱”,不是所謂的“雜音”和“噪音”�。恰恰相反,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為推動社會政治進步所承擔的歷史責任����。盡管在官場嚴重腐敗的背景下,學(xué)界也難于幸免����。但我始終相信,中國知識界中恪守良知�����、擔當?shù)懒x的大有人在���。他們既扎實地立足于中國的具體國情�����,又充分地借鑒人類文明的優(yōu)秀成果�����,以自己的知識和思想貢獻于振興中華的大業(yè)���,一點一滴地推動著國家和民族的進步��。
在今世界����,之所以越來越多的政治學(xué)者日益強調(diào)官民共識或國家-社會的協(xié)同治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
首先��,官民共治是實現(xiàn)善治的基本途徑�����,是通往人類理想政治狀態(tài)的必由之路�。人類已經(jīng)進入一個全球化和網(wǎng)絡(luò)化的新時代,人類的理想政治狀態(tài)也相應(yīng)地從“善政”轉(zhuǎn)變?yōu)?ldquo;善治”��。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過程,其本質(zhì)特征就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或簡稱國家與社會,處于最佳狀態(tài)���,是雙方對社會政治事務(wù)的協(xié)同治理�����。如果從治理主體的角度看��,人類社會至今已經(jīng)有過三種基本形式�����,即自治-官治-共治��。在國家和政府產(chǎn)生前����,人類實行的是原始自治�����。在國家產(chǎn)生后的很長時間中,人類實行的是獨裁專制��,即官治����。進入現(xiàn)代后,官治逐漸讓位于共治���。共治有多種形式���,官民共治是其中的最高形式,官民共治就是民主政治�����。根據(jù)馬克思的設(shè)想�,到了共產(chǎn)主義社會,國家將隨著階級而消亡�����,民主也不復(fù)存在�。即使根據(jù)馬克思的政治邏輯����,民主也是國家存在的最后的也是最高的形式�,官民共治即是通向其理想的無國家無民主的必經(jīng)之路�。
其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已經(jīng)發(fā)生深刻的結(jié)構(gòu)性變化����,社會形成了三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tǒng)。即以黨和政府官員為代表�����,以黨政組織為基礎(chǔ)的國家系統(tǒng)�,或稱政治社會;以企業(yè)家為代表�����,以企業(yè)組織為基礎(chǔ)的市場系統(tǒng)���,或稱經(jīng)濟社會�����;以公民為代表���,以民間組織或社會組織為基礎(chǔ)的社會系統(tǒng)��,或稱公民社會�。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社會變遷進程中�,我們已經(jīng)可以明顯地看到,市場系統(tǒng)和社會系統(tǒng)的力量正在迅速成長��,特別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后�����,一個相對獨立的中國公民社會開始形成����,并且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發(fā)生日益重要的影響。隨著社會力量的日益增長�,國家將不斷地還政于民,還權(quán)于社會��,這是一個不可逆轉(zhuǎn)的社會政治進程��。國家-社會的協(xié)同治理或官民共治�����,不過只是國家還權(quán)于民的實現(xiàn)形式��。我曾經(jīng)說過���,縱使有天大的中國特色���,我們對此也不能例外。因此��,官民共治是社會變革和政治進步的必然結(jié)果����。
最后,在一些公共領(lǐng)域�����,我們正面臨嚴重的治理困境�����,急需重建新的治理秩序����。在公共治理領(lǐng)域�,最佳的政策效果是“帕累托最優(yōu)”��,即政策相關(guān)方只有利益的增加�,而無利益的損失。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后果即是截然相反的情況:利益相關(guān)者都成為利益損失者�����,都對相關(guān)政策不滿意��。我把利益相關(guān)方都成為輸家的政策困境�����,稱為“城管困境”�����。因為“城管”現(xiàn)象是這類政策的典型案例:管人者與被管者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雙方都不滿意。人們怪罪于“城管人員”�����,但城管人員同樣也冤屈滿腹。一種政策如果沒有贏家只有輸家��,無疑是最壞的政策��。在現(xiàn)實生活中���,仔細觀察就會發(fā)現(xiàn)這樣的情況到處可見。如“醫(yī)鬧”��,大夫擔驚受怕�,而患者則含怨藏怒。再如學(xué)校教育�����,學(xué)生��、家長��、老師都牢騷不斷��。更廣泛地說���,我們的維穩(wěn)代價越來越高���,而不穩(wěn)定因素卻日益增多���;居民的民生不斷改善,而人們的對政府的滿意度和信任度卻沒有隨之提高�����;舉國上下都痛恨官員腐敗����,但腐敗卻仍在高位區(qū);一方面�����,我們提倡公共服務(wù)的均等化���,另一方面我們卻又在政策上助長各地公共服務(wù)的差異化�����。凡此種種�,都是治理的失序、失效和碎片化�����,是我們面臨的治理困境��。任何一位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負有責任的官員和學(xué)者都必須正視公共治理的這些挑戰(zhàn)����,并通過深化政治改革�,切實推進民主法治,從體制機制上來解決這些問題���,破解治理的困境��。
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四種可能的效果���。其一是政策相關(guān)方都從中獲益,而沒有任何損失�����,即全贏的局面����。其二是多數(shù)利益相關(guān)者從該項政策中獲益���,而少數(shù)人的利益受損,即多贏少輸?shù)木置?。其三是少?shù)相關(guān)者獲益而多數(shù)人的利益受損,即多輸少贏的局面�。其四是政策相關(guān)者的利益均不同程度受損,即全輸?shù)木置?���。任何理性的決策者都應(yīng)當力爭第一種結(jié)果,而堅決避免最后兩種結(jié)果��,特別要杜絕最壞的“城管困境”���。如何從根本上走出目前的治理困境��?根本的途徑就是重構(gòu)公共治理秩序�����,努力實現(xiàn)官民共治或國家社會的協(xié)同治理�。根據(jù)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切實推進官民共治,有以下幾個著力點�。
第一,確立核心政治價值�����,重構(gòu)政治認同����。核心政治價值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政治認同的基礎(chǔ),也是民主治理的根本價值所在��。核心政治價值也應(yīng)當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主要內(nèi)容�。它既要傳承我國優(yōu)秀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更要體現(xiàn)人類政治文明的發(fā)展方向����。我認為,從民主治理的角度看�,自由、公正��、尊嚴����、和諧��,就是我們應(yīng)當努力弘揚的核心政治價值��,也是官民共治的價值目標��。
第二����,改造公民教育���,強化公民在公共治理的主體意識�����。“人民當家作主”這一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價值�����,在現(xiàn)代民主法治條件下�����,只有體現(xiàn)為具體的“公民身份”或“公民權(quán)利”�,才能真正實現(xiàn)。黨的十七大指出:要“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政治教育的重點應(yīng)當是公民教育,通過政治教育強化公民的主人翁精神���,樹立公民的權(quán)利意識���、法治意識、公正意識��、責任意識和主體意識����,自覺擔當起公共治理的責任���。
第三���,強化執(zhí)政道德���,再造政治信任。我們既要強調(diào)執(zhí)政能力和執(zhí)政地位�,但同樣要強調(diào)執(zhí)政倫理。共產(chǎn)黨的執(zhí)政地位既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打天下坐天下”是舊政權(quán)的邏輯���,不應(yīng)當是作為先鋒隊組織的共產(chǎn)黨的執(zhí)政邏輯���。“權(quán)為民所有”、“權(quán)為民所賦”和“權(quán)為民所用”�,才是黨執(zhí)政的合法性來源。因此���,官民共治完全符合中國共產(chǎn)黨的執(zhí)政宗旨�。
第四,完善制度環(huán)境�,擴大公民參與。公民參與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沒有廣泛的公民參與��,就談不上官民共治����。有序的和有效的公民參與,需要相應(yīng)的制度保障�,需要有足夠的合法渠道。隨著公民物質(zh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其公共參與的需求日益增多�。與公民政治參與的需求相比�����,我們的制度建設(shè)明顯滯后�����,參與渠道遠遠不夠��。我們應(yīng)當盡快建立和完善官民共治的制度框架�,讓更多的公民通過合法的方式有序地參與公共生活的管理。
第五��,創(chuàng)新社會管理��,推進社會自治��。自治也是民主政治的要素���,尤其為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所重視��。社會自治在我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和深厚的現(xiàn)實基礎(chǔ)����,有可能成為官民共治的一個突破口�����。在舉國上下正在大力推行的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中��,社會自治也應(yīng)當是重要的關(guān)節(jié)點����。社會自治應(yīng)當特別注重基層地方自治和行業(yè)職業(yè)自治�。無論哪一種類的社會自治���,都必須充分發(fā)揮社會組織或民間組織的重要作用�。
總而言之��,官民共治或國家社會的協(xié)同治理��,就是政府組織與民間組織共同承擔起公共治理的責任����。從狹義上說,它是推進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改善社會治理狀況的關(guān)鍵所在。從廣義上說����,官民共治也是推進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