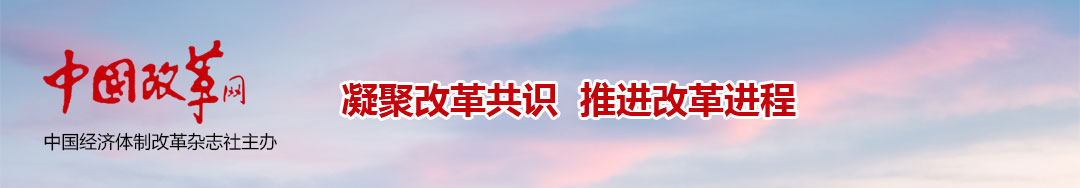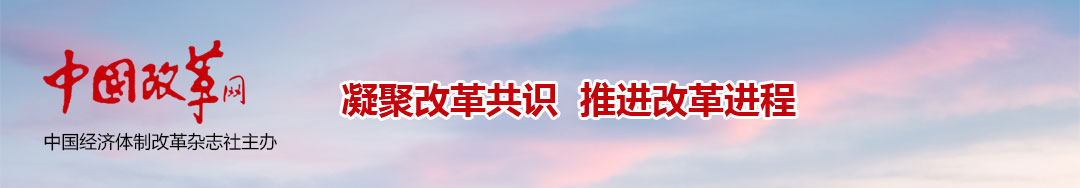編者按:吳敬璉和青木昌彥分別是中日泰斗級的經(jīng)濟學家�����。吳敬璉曾五獲中國經(jīng)濟學界的最高獎項“孫冶方經(jīng)濟科學獎”;青木昌彥則一直任教于國際一流大學,曾榮獲“熊彼特獎”��,在比較經(jīng)濟學以及公司治理理論方面有著卓越的貢獻�,同時也是較早關(guān)注中國經(jīng)濟的西方經(jīng)濟學家之一�。兩人最初相識于1994年的京倫飯店會議上。2005年夏天��,中日的財經(jīng)媒體聯(lián)合舉辦了一場兩位經(jīng)濟學家的對話��,共論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變遷��。十年后的今天��,日本依然沒有走出低迷的困境���,中國雖然已經(jīng)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但經(jīng)濟下行的壓力愈發(fā)凸顯���。在中國經(jīng)濟步入“新常態(tài)”的背景下���,兩位經(jīng)濟學家再次相聚北京�,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組織的中日經(jīng)濟學家學術(shù)交流會上�����,共論中日經(jīng)濟與改革����。
本次交流會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與野村綜研金融市場研究委員會(NRI)聯(lián)合舉辦,會議主題為“中日經(jīng)濟的改革與比較”�����。研討會上���,CF40學術(shù)顧問����、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吳敬璉與斯坦福大學經(jīng)濟學教授青木昌彥就中國經(jīng)濟“新常態(tài)”以及中日經(jīng)濟改革與比較等領(lǐng)域�,進行了深入對話。
當前正在進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對30多年改革中形成的經(jīng)濟體制和發(fā)展模式的進一步改革����。作為當前改革對象的原有經(jīng)濟體制和發(fā)展模式����,和日本戰(zhàn)后建立的經(jīng)濟體制和發(fā)展模式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兩國的改革在一些方面可以相互借鑒。
中國早期對改革目標模式的探索
中國在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后就開始改革開放�,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扭轉(zhuǎn)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造成的體制危機和經(jīng)濟衰敗����,制定了對應的救亡圖存辦法。開始時并沒有明確的目標�����,采取的辦法是陳云提出的“摸著石頭過河”���,即走一步看一步,試驗成功后再加以推廣��。但與此同時����,有人在思考����,除了進行一些變通性的政策調(diào)整之外��,在經(jīng)濟體制和發(fā)展方式上都要選定自己的目標模式�����。
因此�����,從上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到80年代上半期��,在中國展開了討論�。對于改革目標模式選擇,存在三種選項:第一種是蘇聯(lián)����、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模式。從本質(zhì)上說���,也就是所謂“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它的特點是在保持國有制的統(tǒng)治地位和計劃經(jīng)濟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加大市場對企業(yè)的引導和激勵����,來提高企業(yè)的積極性。第二種是東亞模式��,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導的市場經(jīng)濟�����。第三種模式是受過西方經(jīng)濟學教育的學者主張的歐美自由市場經(jīng)濟模式��。
從上世紀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比較時興的是蘇東模式�����,許多官員和經(jīng)濟學家都特別熱衷于介紹蘇聯(lián)的柯西金改革、匈牙利的改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但這種模式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原因一方面是改革沒有取得成功,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即使做得最好的匈牙利也陷入了危機��。另一方面����,在理論上提倡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的學者也紛紛否定了自己的看法。所以����,中國只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進行了一段試驗。這就是從四川開始進行�����、后來推廣到全國的國有企業(yè)擴大企業(yè)自主權(quán)的改革����。其基本特征和蘇聯(lián)東歐的改革相類似。但這個改革也沒有取得成功�����,相反引起了財政和通貨膨脹問題,到1981年后就被多數(shù)人所否定了��。
“東亞模式”在80年代的目標模式選擇中勝出����,為多數(shù)人所接受,經(jīng)濟發(fā)展也沿著“威權(quán)發(fā)展主義”(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的路徑進行�����。至于第三種模式�����,把自由市場經(jīng)濟看作改革最終目標的學者也承認�����,在市場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情況下�����,用市場來配置資源和進行激勵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們達成共識�,至少在改革初期要采用政府主導的市場經(jīng)濟模式��。
在1978年開辟中國改革的第一個中央會議前——即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派出了許多考察團到各國去“取經(jīng)”�。影響最大的一個是鄧小平1978年對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的考察�����。在這三個國家中�����,他最欣賞的是新加坡�,不但是指新加坡的對外開放和特區(qū)政策,更欣賞新加坡在強有力的政府管制下的嚴整社會秩序���。這種威權(quán)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jīng)濟是鄧小平欣賞的模式����。在干部和群眾中具有更廣影響的是以理論家��、政治家鄧力群和重要經(jīng)濟官員馬洪等為首的國家經(jīng)委代表團同年11月對日本的訪問和考察���。鄧力群�、馬洪等寫成的考察報告《訪日歸來的思索》對日本的經(jīng)濟社會體制贊譽有加,在領(lǐng)導干部和國有企業(yè)的管理人員中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鄧力群在書中得出結(jié)論���,要學習日本在政府的管控之下發(fā)展商品經(jīng)濟���。商品經(jīng)濟的想法最早是由鄧力群的日本考察在中國的中上層干部里普及開來的。
“半市場���、半統(tǒng)制”的經(jīng)濟體制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和日本的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建立的歷史背景存在重大區(qū)別��。日本的戰(zhàn)后體制���,是在明治維新“脫亞入歐”和戰(zhàn)后民主改革的基礎(chǔ)上演變而來�。中國的經(jīng)濟體制則是從蘇聯(lián)式的集中計劃經(jīng)濟體制(State Syndicate 或Party-State Inc.)演變而來���。因此���,在中國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jīng)濟”和“威權(quán)發(fā)展主義模式”中����,政府的主導作用更加無所不包和強勁有力���。
總體來說,日本是以私有經(jīng)濟為主體��,而中國始終是以國有經(jīng)濟為主要經(jīng)濟成分�����,即使到今天��,許多人還是力主遵循列寧1921年關(guān)于共產(chǎn)黨必須“控制制高點”的教導����。1920年蘇聯(lián)轉(zhuǎn)入新經(jīng)濟政策,恢復市場經(jīng)濟�,黨內(nèi)有人懷疑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并且會損害布爾什維克黨的領(lǐng)導力��。1921年列寧在共產(chǎn)國際大會上就對政策的懷疑和反對做出回答�����,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其特殊性在于�����,黨和政府控制著“制高點”���,一切經(jīng)濟活動都是在政府所規(guī)定的范圍內(nèi)進行�,而且隨時可以改變���。在中國出版的列寧著作里����,“制高點”一詞被翻譯成命脈�,所以我們的文獻里常見的提法是,國家和國有企業(yè)必須控制國民經(jīng)濟命脈����。
1984年和1987年的體制設(shè)計雖然提出要發(fā)展商品經(jīng)濟,同時又強調(diào)政府的計劃控制����。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chǔ)上的有計劃商品經(jīng)濟”����。1987年中共十三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報告里提到: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jīng)濟的運行機制應當是“國家調(diào)節(jié)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è)”的機制����。上述機制是由國家計委的幾位領(lǐng)導干部在1986年提出的����,十三大接受了這個意見。到現(xiàn)在�����,很多人還認為這是對市場經(jīng)濟很好的描繪����,但在我看來并不是這樣。這個提法存在很大缺陷:雖然企業(yè)是由市場引導�,但是市場是由國家和政府調(diào)節(jié),這就埋下了伏筆���。到了21世紀��,許多文件里出現(xiàn)了“黨和政府要提高駕馭市場的能力”的提法�����。這表明�,雖然1992年已經(jīng)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改革目標,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里的市場����,只是國家所駕馭的工具���。
1992年的中共十四次代表大會確立了市場經(jīng)濟的目標���。江澤民總書記在1992年6月9日中央黨校的講話中說,對于改革所要建立的經(jīng)濟體���,有多種提法����,包括“計劃與市場相結(jié)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jīng)濟體制”、“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jīng)濟體制”���、“社會主義的市場經(jīng)濟體制”等等����。他說自己傾向于“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提法��。后來�����,中共十四大確認了這個提法�����。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根據(jù)十四大的決定制訂了建設(shè)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行動綱領(lǐng)����,即有名的《關(guān)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若干問題的決定》(“50條決定”)���。這是一個全面改革的綱領(lǐng)�����,要求在20世紀末形成“統(tǒng)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市場經(jīng)濟的理解��,與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的理解非常接近����,這可能反映了經(jīng)濟學家對文件起草的影響�����。不過��,在實際生活中,強調(diào)政府主導作用的思想仍然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由于這種影響的存在,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在20世紀末形成“統(tǒng)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的要求實際上并沒有實現(xiàn)。中國在20世紀末建立起來的體制是一種“半市場��、半統(tǒng)制”體制�����,它的“半統(tǒng)制”性質(zhì)主要表現(xiàn)為:國家部門����,包括各級黨政機關(guān)和國有企業(yè)仍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21世紀初期“中國向何處去”的大辯論
舊體制因素的強化造成了一系列社會矛盾的激化,其中最為突出的兩個問題��,一個是腐敗活動日益猖獗���,直至侵入黨政軍組織的機體���;第二個是粗放發(fā)展導致社會經(jīng)濟問題愈演愈烈���。蘇聯(lián)在上世紀60年代后期提出增長方式要從粗放增長方式(extensive growth, 即靠投資驅(qū)動的增長)向集約增長方式(intensive growth,即以效率提高為動力的增長)轉(zhuǎn)型。粗放增長方式的關(guān)鍵問題在于效率太低�,需要提高全要素生產(chǎn)率(TFP)對增長的貢獻。
中國是在1995年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時提出需要實現(xiàn)增長方式轉(zhuǎn)變的�����。“九五”計劃正好是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后推進全面改革的時期���,各方面的體制都有所進步���,增長模式轉(zhuǎn)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十五”(2001-2005)計劃期間���,情況發(fā)生了逆轉(zhuǎn)��,中國城市化加速�,政府手里掌握了大量土地資源����,于是政府對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主導作用變得越來越強�����,經(jīng)濟的發(fā)展方式也變得越來越粗放��。因此�,政府在制定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時���,重新提出要把轉(zhuǎn)變經(jīng)濟增長方式作為十一個五年計劃的主線�����,但是沒有能實現(xiàn)�����。到“十一五”最后一年中央提出�,“加快經(jīng)濟增長方式轉(zhuǎn)變刻不容緩”����。不過�,十二五計劃期間���,經(jīng)濟轉(zhuǎn)變?nèi)匀徊皇呛苊黠@。資源短缺�、環(huán)境破壞,宏觀經(jīng)濟上的貨幣超發(fā)�����、債務積累���、杠桿率升高以及社會矛盾都日趨嚴重���。
于是,再次爆發(fā)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大爭論:是依靠重啟市場化的經(jīng)濟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來從根本上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還是強化政府作用�����,推行以強勢政府為主要特征的所謂“中國模式”�����。
在相當長時間里�����,后一種意見占居優(yōu)勢,直到十八大前夕到達最高峰�。但是,強化政府的管控和國有經(jīng)濟的主導地位不僅沒有解決剛才提到的問題���,反而使得問題越來越嚴重����,矛盾越來越尖銳��。
在這種情況之下���,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問題做出了正確的回答�。十八大提出��,“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地深化重要領(lǐng)域的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實現(xiàn)國家各項工作的法治化”。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ān)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fā)揮政府的作用”�����。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jù)市場規(guī)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xiàn)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yōu)化”。“建設(shè)統(tǒng)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chǔ)”���,必須按照上述要求加快形成“企業(yè)自主經(jīng)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xiàn)代市場體系”。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部署的336項改革��,就是圍繞這些要求提出的�����。
確立“新常態(tài)”的核心問題是提高增長質(zhì)量
現(xiàn)在面臨的問題則是����,在確立“新常態(tài)”的過程中如何貫徹十八大決定。中國所謂的“新常態(tài)”并不是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M.A. El-Erian所說的長期蕭條的“新常態(tài)”����。按照中國領(lǐng)導歷次講話,“新常態(tài)”需有兩個特征:一是“由高速增長轉(zhuǎn)向中高速甚至是中速增長”�;一是“由粗放發(fā)展方式轉(zhuǎn)向質(zhì)量效益型的集約發(fā)展方式”。這兩個基本特征都用了“轉(zhuǎn)向”的說法��,但是“轉(zhuǎn)”的進度有明顯的差別:其中前一個GDP增速下降已經(jīng)是既成事實���,而后一個即發(fā)展模式轉(zhuǎn)變�,或結(jié)構(gòu)改善、效率提高�,還需要經(jīng)過艱苦努力才能實現(xiàn)。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轉(zhuǎn)變經(jīng)濟發(fā)展方式由粗放發(fā)展到集約發(fā)展的轉(zhuǎn)變是制定“九五”(1996-2000)計劃時提出來的�����,到今年已經(jīng)整整20年���,還沒有實現(xiàn)���。可見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在總結(jié)十五計劃時���,我們曾經(jīng)進行了一場大討論,所有原因歸結(jié)起來就是體制性障礙�,最大的體制性障礙則是政府的主導地位,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有很多具體表現(xiàn)。
我對媒體把“穩(wěn)增長”放在經(jīng)濟工作的首位有些懷疑����。我認為應該把依靠改革提高經(jīng)濟增長質(zhì)量放在首位。當然也要做到保底線�,所謂的保底線是指,保持有一定質(zhì)量的增長速度����。但是保底線不是靠刺激政策能解決的。現(xiàn)在有一個對業(yè)界和學界都很有影響的看法是����,保增長底線還是要靠擴張性貨幣政策或增加投資來解決,我認為這個辦法不可行��。
我們當前面臨的問題是趨勢性���,而不是周期性的�。我想引用野村證券辜朝明先生關(guān)于近年來各國發(fā)生的金融危機實質(zhì)上是資產(chǎn)負債表衰退的分析來說明我們當前面對的問題����。我們的資產(chǎn)負債表存在重大缺陷,杠桿率太高����。當泡沫不能支撐而破滅之際�,就會出現(xiàn)流動性陷阱:所有人都不愿意借債�����,也不愿意投資�����,于是貨幣流通速度大大降低���。即使要用擴張性貨幣政策來刺激,也很難收到提振經(jīng)濟的效果����。我覺得他的說法也有一定道理,貨幣政策是不行的����。其實最近一年來,流動性是相當寬松的��。當人們沒有投資意愿�����,發(fā)行再多的貨幣都是往股市去,而沒有投資于實體經(jīng)濟���。
中央經(jīng)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強財政政策的力度,我贊同這個意見�。但是,加強財政政策的力度要落腳到強化信心和提高投資積極性����,而不是單純增加財政支出,用擴大需求去拉動經(jīng)濟增長���。
國有企業(yè)改革勢在必行
1997年召開的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及1999年召開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都對國有經(jīng)濟改革提出了要求�����,強調(diào)要對國有經(jīng)濟進行布局調(diào)整�。有關(guān)國企改革的決定在文字上保持了“以國有為主導”的提法��,但對原來的提法做了新的解釋���,說明“主導”并不是處處都要控制。十五次代表大會的說法是��,“對關(guān)系國民經(jīng)濟命脈的重要行業(yè)和關(guān)鍵領(lǐng)域�����,國有經(jīng)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lǐng)域����,可以通過資產(chǎn)重組和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chǎn)的整體質(zhì)量��。”1999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關(guān)于國企改革的決定����,把“關(guān)系國民經(jīng)濟命脈的重要行業(yè)和關(guān)鍵領(lǐng)域”進一步規(guī)定為三個行業(yè)一個領(lǐng)域,即關(guān)系國家安全的行業(yè)�,自然壟斷行業(yè),提供公共產(chǎn)品和公共服務的行業(yè)���,還有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和重要行業(yè)的骨干企業(yè)���。有關(guān)決定要求按照上述原則對國有經(jīng)濟進行有進有退的布局調(diào)整。但是�����,2006年國資委發(fā)布了一個據(jù)說是國務院批準的文件�,要求加強國有企業(yè)的控制,在7個行業(yè)進行絕對控制����,在9個行業(yè)保持較強的控制。這實際上是加強了國有經(jīng)濟�����。剛才我已經(jīng)談到����,雖然國有企業(yè)已經(jīng)上市�����,但還是按照國資監(jiān)管條例執(zhí)行——人�����、事和資產(chǎn)都是國資委來管理��,高管也是國資委或中央組織部任命�。
最近拉迪教授(N. Lardy)在他的新著里說����,中國的私營企業(yè)已經(jīng)占據(jù)主導地位,今后這種主導地位還會不斷增強���。我覺得他可能過分注重了私營企業(yè)主中國經(jīng)濟中的數(shù)量比重��,忽略了以下兩個情況:一是國有企業(yè)在數(shù)量上雖然比不上民營企業(yè)����,但在重要部門占有絕對優(yōu)勢��,二是大型私營企業(yè)也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有些甚至受到政府官員的控制?��?傊?,國有企業(yè)如何改革�����,與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和解決根本性問題是息息相關(guān)的���。
當然其他改革也很重要����,例如法治����,這在中國一直是一個問題。關(guān)于Rule of Law還是Rule by Law�,我認為不要把法治(Rule of Law)變成法制(Rule by Law)。當然真正做到這點很不容易�,牽涉到很多問題。
(作者系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本文為作者于2015年3月25日在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與野村綜研金融市場研究委員會聯(lián)合舉辦的“中日經(jīng)濟學家學術(shù)交流會”上所做的主題演講����,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秘書處整理����,經(jīng)作者審核。)